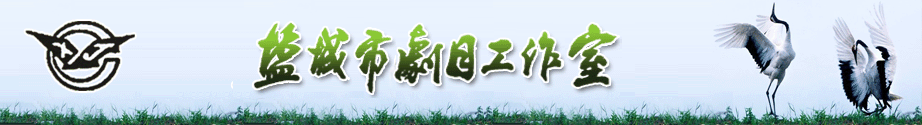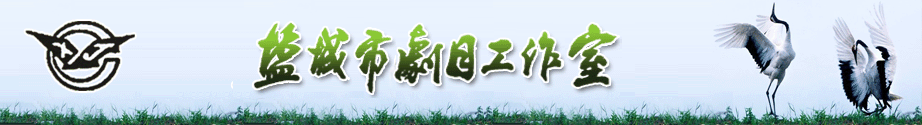學術(shù)論文之二
(原文發(fā)表在上海同濟大學《中華藝術(shù)論叢》2011年4月 第十期(振興戲曲專輯)上)
文化興替與戲曲重組的歷史變遷
徐柏森
中國戲曲始終承繼歌舞演故事的形態(tài),,并以其強烈的延續(xù)能力,,滿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。戲曲能夠生生不息的原因很多,,但值得注意的是,,每次急劇更替的焦點,,多集中在地域新文化的興起上。而地域新文化的興起,,從史的角度考察,,又和它域文化的融入息息相關(guān)。再從當前和未來考慮,,域外文化的涌動,,既能改變某地的文化格局,也能對某地之戲曲產(chǎn)生巨大的影響力,。因此,,重視地域新文化的興替,關(guān)注域外文化的融入和輸出,,直接關(guān)系到戲曲的構(gòu)建和重組,。
一、從歷史角度考察:來自地域文化和它域文化的作用力,,在撞擊融會過程中,,不斷地完善和發(fā)展了戲曲的本體。
我國古代文化,,受當時地理條件的限制,,發(fā)展不盡平衡。這種地理環(huán)境的差異,,造成了各地風俗民情的不同,。加上作家、藝術(shù)家不同秉賦,、氣質(zhì),,又形成多樣的創(chuàng)作風格。戲曲的成形和發(fā)展,,基本上受地域文化的影響,,呈蛻變狀態(tài)。它的緩慢推移,,使“新聲倚舊聲”的傳統(tǒng)不斷延續(xù),。戲曲聲腔、語言、表演的凝聚力,,鑄就了戲劇文化發(fā)展的穩(wěn)定基質(zhì),。這是問題的一面。另一面,,當戲劇處于新舊交替的碰撞下,,或突然遇到來自它域的新腔新調(diào)、新的表演方法的剌激,,也會造成張力的膨脹,,以至促成新陳代謝的加劇。故而我們應關(guān)注來自地域和它域的相互作用力,。
(一)元代以前的準備階段
漢代早有正樂與散樂之別,,正樂屬官方宴饗所用,散樂系民間歌舞,、雜耍,。當時民間散樂豐富多彩,到處受人歡迎,。漢武帝劉徹覺察這情況,,在后庭不僅設樂府,而且對民間散樂“廣事收集,,務必征調(diào),。”散樂滲入宮廷,,使正樂遭受撞擊,,并產(chǎn)生融會。
隋代《龜茲樂》盛行,,律譜為新聲,,又與民間樂伎彼此融會,則別有一番發(fā)展,。
唐代進一步發(fā)展這種融會,,使《龜茲》、《西涼》的音樂,、舞蹈廣泛融入唐代歌舞戲中,。唐中葉尤甚,玄宗擅打羯鼓,,號稱“皇帝梨園弟子”就是一個明證,。另外,,唐代的參軍戲,,是另一種形式,它源于故事,,近于科白的表演,,以滑稽,、戲謔為主要手段。
宋代又有了變化,,民間瓦子勾欄雜劇的興起,,標志中國戲曲的初級形態(tài)漸趨完成。北宋時,,東京市井轟動一時的《目蓮救母》雜劇,,就是一例。另說:“晉南翼城金元墓葬《目蓮救母》戲曲中,,至今完整地保留著古代新疆于闐的曲調(diào),。”這兩據(jù),,一是市井轟動,,連演七八天;一是該劇樂舞豐富,,甚至保留著異域的聲腔,。
南宋時,情況就更不同了,。南宋時勾欄技藝與教坊雜劇較北時更甚,,雜劇在臨安得到較大發(fā)展,官方所謂教坊的設置,,皆勾欄藝人在內(nèi)庭表演,,或民間征調(diào)。史書上有“官本雜劇”一稱,,應解釋為通行之本,,如我們說“官話”為“普通話”之意相似。
由于雜劇的空前盛行,,促成了后來南戲的誕生,。南戲所唱為南方曲調(diào),故名“南戲”或“南曲,�,!蹦戏铰暻慌c閩、浙語音,,區(qū)別于東京勾欄雜劇聲腔及中原語音,,遂產(chǎn)生了新的魅力,因而在南方取代了勾欄舊腔,。
與此同時,,北方的金,又是一番情景。燕京在異族統(tǒng)治下,,別是一種繁華,。諸宮調(diào)這一體制的興起,是北方地域的產(chǎn)物,。諸宮調(diào)起于故事說唱形式,,然后再由說唱故事進入表演故事。因其地域在黃河以北,,故又稱其為“北曲”,。北曲做為聲腔,為后來的元雜劇奠定了根基,。此外,,南宋時西南地域也出現(xiàn)了“川鮑老”、“川雜劇”及成都的“撼雷”等演出,,亦甚為繁盛,。這是另一地域的局部現(xiàn)象,且影響較小,。
中國戲曲形成較晚,,有一定社會原因。古代文化結(jié)構(gòu)上,,存在重抒情,、輕敘事的特點。對詩歌,、音樂,、舞蹈的發(fā)展,無疑是一種促進,,而對戲劇只有到了說唱音樂的興起,,才做好了成形的準備。元代以前,,漢,、唐時,樂舞得到高度發(fā)展,,而宋時,,勾欄雜劇及南戲、諸宮調(diào)等在民間興起,,這些都是地域文化與它域文化相互融會的產(chǎn)物,,也是多方的共同作用力,促成了戲曲的誕生,。
(二)元代以后的發(fā)展階段,。
戲曲在元代正式確立了地位,。雜劇開創(chuàng),產(chǎn)生民間,,主要作者皆民間藝人,作品樸素,、通俗,、以本色見長,文人是后來參與其事的,。后世推崇的關(guān)漢卿,、馬致遠、白樸,、鄭光祖四大家,,還有王實甫、喬吉,、費唐臣等人,,都是在反映現(xiàn)實,對當時悲慘黑暗的社會采取對抗態(tài)度上,,表現(xiàn)了作家思想意識中的人民性及民族傾向,。作品借著雜劇這一體制,發(fā)泄了對異族殘暴統(tǒng)治的不滿,,符合了當時人民的意愿,。
元滅南宋后,雜劇南移,,南戲北上,,產(chǎn)生了戲曲文化較大規(guī)模的交流。南戲和雜劇在聲腔上不同,,演唱形式也不同,,雜劇有弦索伴奏,而南戲聲腔沒有一定的宮譜,。只用打擊樂按節(jié)拍隨聲轉(zhuǎn)調(diào),,尾段或尾句用二人或多人同聲合唱而已。后來南戲《琵琶記》有了弦索譜腔,,且南北通行,,因而稱之為“弦索官腔”。
明代的傳奇繼承南戲的傳統(tǒng),,流行于明初的《琵琶記》,、《荊釵記》、《劉知遠白兔記》,、《拜月亭記》,、《殺狗記》等,,皆系元代作品。南戲至傳奇是一脈相承的,,其重要劇目對后世戲曲文化的影響較大,。但是傳奇宣揚禮教的傾向,漸使觀眾感到厭倦,,對戲曲八股早成腐臭的形式,,也感到難以接受,因此中葉以后,,慢慢轉(zhuǎn)變到注重人性,,描摹世態(tài)上來。此外,,明代另一脈是繼承了元雜劇的明雜劇,。
明代時,江,、浙,、湖、廣一帶,,已有各自地區(qū)民歌小曲和語言結(jié)合較緊密的新腔出現(xiàn),,如海鹽腔、余姚腔,、弋陽腔之類,,不僅在源流上各具來歷,而且已擁有地域觀眾,。海鹽腔,、余姚腔后來衍變成昆山腔,昆山腔又集南北二曲之長,,取代了南北曲,。顯赫一時的南戲和雜劇,至此讓位給新興的昆腔了,。昆山腔源出江蘇昆山,,由曲師魏良輔創(chuàng)興。梁辰魚的《浣紗記》,、湯顯祖的《玉茗堂四夢》,、沈璟的《屬玉堂傳奇》等作品的相繼問世,奠定了昆山雅音的特殊地位,,于是昆曲身份漸顯。但明代另一聲腔勁旅,,江西弋陽腔,,因其結(jié)構(gòu)靈活,,善于流傳,也得到較大發(fā)展,。昆,、弋長期對峙,各自都有不同的發(fā)展,,顯示了地域文化不斷發(fā)生的新質(zhì)新態(tài),。
清初延續(xù)了這一對峙,并進一步發(fā)展到兩腔爭勝的局面,。昆腔到了清代,,已逐漸脫離群眾,,傳奇劇目大多成為官紳,、地主的家樂,,只做雅音欣賞,,一班士大夫皆認昆腔為正統(tǒng)。弋腔闖蕩江湖,,貫通南北,,始終不離人民群眾,,因而在民間發(fā)展迅猛,對后來各地方劇種的興起有極大的影響,。弋腔在北方扎根以后,則更為流行,,被認為是燕俗之劇,,又與北京語言、土戲相結(jié)合,,改稱“四平腔,。”
從漢代百戲至清初聲腔演變,,可看出地域文化和它域文化對戲曲構(gòu)建的巨大影響,。戲曲文化的屬性,離不開民族,、民間的地域條件,它的本體應是中華大地各民族文化不斷撞擊,、不斷融會的產(chǎn)物,。這種血肉相連的特殊關(guān)系,,造成了生生不息、代代相傳,、越衍越繁的戲曲景觀,。
二、從劇種現(xiàn)狀觀察:地方戲的繁興,,加劇了地域特征與它域特征的區(qū)別,并且呈現(xiàn)出一定的互斥性,,從而推動劇種個性的確立,。
戲曲在延續(xù)過程中,舞臺演出發(fā)展了戲曲的技藝,,呈現(xiàn)出演技的共性特征,。如綜合性、虛擬性,、程式性的運用,,直至現(xiàn)在這些特征越來越明顯地表明戲曲與其它戲劇的區(qū)別。另一方面,,地方劇種的繁興,,又造成了劇種之間的互斥,它們雖同屬戲曲家族,,然而又各自獨立,,形成“你不能代替我,我不能代替你”的局面,。它們各自成立一個系統(tǒng),、自轄一塊領(lǐng)地,自成一種氣候,、自述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,。從地域文化的大背景看,這種互斥不僅是劇種個性的體現(xiàn),,也可以認做是一種地域文化所共有的現(xiàn)象,。
(一)蒲松齡的貢獻。
清代重要作家蒲松齡,,除寫《聊齋志異》成為家喻戶曉的傳世珍品外,,他還開拓了戲曲創(chuàng)作的另一天地。他寫過鼓兒詞,、俚曲,、,俚曲就是用北方民歌小曲和山東淄川土語寫的地方戲,。在蒲氏之前,,文人墨客只用南北曲作劇,,而在昆、弋流行時,,用土曲土語寫地方俚曲者,,蒲氏則是第一人。
清初戲曲聲腔,,有“南昆北弋,,東柳西梆”的說法�,?梢姷赜蚵暻灰呀�(jīng)繁興,。昆腔因《桃花扇》、《長生殿》而得以暫時回升,,但好景不長又衰落下去,,主要因其文辭艱深、唱腔高雅,,和者愈寡,。弋陽腔通過徽池調(diào)或青陽腔的“加滾”,,又對高腔,、梆子腔產(chǎn)生影響,高腔又與陜西地方聲腔結(jié)合產(chǎn)生秦腔,。梆子腔轉(zhuǎn)而在山西,、陜西等地落戶,成為梆子系統(tǒng)的始源,。梆子系東路聲腔,,它包括北方民歌小曲、昆曲,、青陽,、羅羅、亂彈,、西皮,、二黃諸調(diào),內(nèi)容比較豐富,。梆子腔的興起,,與蒲松齡寫《禳妒咒》有關(guān),這是梆子較早的劇本,。蒲氏開創(chuàng)用土語寫戲的先河,,隨之各地文人、舉子也都相繼效法,,使地方戲更具地方特點,。
(二)乾隆年間地方戲的激烈競爭,。
弘歷曾以南巡名義,六次離開北京到揚州,、浙江一帶游玩,。每次都把各地較好的伶人帶回北京,充實,、改組其內(nèi)庭演劇班子,。揚州鹽商為迎接弘歷南巡,曲意奉承,,大開排場,,備演大戲。其盛況當時稱為“花雅爭勝”,,,。雅即昆山腔,花為京腔,、秦腔,、弋陽腔、梆子腔,、羅羅腔,、二黃調(diào),統(tǒng)謂之亂彈,。于是花雅兩部爭寵揚州,,后來又發(fā)展到北京。
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(公元1778年至1779年)以魏長生為首的四川秦腔在北京流行,。魏長生藝兼文武,,能劇甚多,入京以《滾樓》一劇唱紅北京,。魏長生的成功是新興的四川地方劇種,,對舊京腔六大班的否定。這一事實充分說明,,戲曲競爭的互斥性是普遍存在的,。四川秦腔系根據(jù)陜西秦腔作四川地方語音的唱腔,而陜西秦腔又和弋陽腔有關(guān),,應看作是花部的發(fā)展,。
乾隆五十五年(公元1790年)弘歷八十歲生日,浙江鹽務大臣征集安徽三慶班入都祝壽,,由是成為著名的“四大徽班進京”事,。三慶班壽期后,留在北京戲園,接踵而來的有四喜,、和春,、春臺,后人稱為四大徽班,�,;瞻嘁云淝f重、優(yōu)美的二黃唱腔,,及媲美雜技的非凡武功,,贏得了北京的觀眾,,站穩(wěn)了腳跟,。魏長生所唱秦腔僅流行了十年光景,即被徽班進京所取代,,可見此時地方戲曲的競爭是何等激烈,。徽班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,,吸取魏長生秦腔失敗的教訓,遂一面發(fā)展二黃及武戲的優(yōu)勢,,另一面則博采眾長不斷豐富自已的技藝,在劇目,、表演,、聲腔上,,融會了昆曲,、楚調(diào)(漢調(diào))、秦腔等劇種的優(yōu)點,,又吸收北京語音及各地牌子小曲,漸漸衍變成劇目豐富,、形式完備、技巧高超的現(xiàn)代京劇,。
(三)京劇的影響與地方戲的繁興,。
京劇的誕生,,在戲曲文化史上有著重要意義,。京劇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劇種,,和它自身藝術(shù)形式的不斷完善,,及流向全國各地有密切關(guān)系,。同治五年,,上海邀請北京皮黃班首次赴滬,,后至光緒年間更趨頻仍,。京劇走向全國,,一方面自身得到發(fā)展,,另一方面也剌激了地方戲曲的自省和提高,。
辛亥革命以后,,京劇發(fā)展已漸趨固化。北京,、上海等大城市是京劇的一統(tǒng)天下,,京劇幾乎成了戲曲的同義詞,可見其影響之大了,。這時,,京劇舞臺相繼出現(xiàn)造詣較高的演員,使京劇的地位又有所加強,。特別是以梅蘭芳為首的四大名旦相繼崛起,,他們競編新戲,在聲腔和表演上不斷進行改革,,形成各具特點的藝術(shù)流派,。京劇對戲曲家族的影響,一直延續(xù)到當代,。目前京劇在北方仍有雄厚的實力,,它的傳統(tǒng)技藝仍對各地方劇種產(chǎn)生影響,故而戲曲家族也把京劇認做是當然的代表,。
以“昆,、高、梆,、黃”四類聲腔流行各地的劇種,,一般比較成熟完備。以民間小曲發(fā)展而來的“二小或三小”戲,,如秧歌,、落子、花鼓,、灘黃等,則較粗陋�,,F(xiàn)按系統(tǒng)分述,,大致如下所示。
1,,“昆,、高、梆、黃”四類聲腔分布情況,。
昆曲——流行江蘇,、浙江、四川,、湖南等地,,或有專唱昆曲戲班,或?qū)υ摰氐胤絼》N產(chǎn)生影響,。
高腔——流行江西,、湖南、浙江,、福建,、廣東、,、四川等地,。產(chǎn)生江西樂平高腔、湖南湘劇,、浙江義烏高腔,、福建蒲仙戲、高甲戲,、梨園戲,、閩劇、廣東潮州戲,、四川時劇,、清音等。
梆子腔——流行陜西,、山西,、河北、河南,、安徽,、山東、四川,、云南,、廣東等地。產(chǎn)生秦腔,、同州梆子,、蒲劇、晉劇,、北路梆子,、上黨梆子,、河北梆子、河南梆子,、越調(diào),、山東曹州梆子、章丘梆子,、萊蕪梆子,、安徽梆子、四川梆子,、云南絲弦,、江西饒河戲、廣東粵劇里的梆黃等,。
皮黃調(diào)——流行安徽,、湖北、湖南,、江西,、四川、云南,、廣東,、廣西等地。產(chǎn)生徽劇,、漢劇,、湘戲、饒河戲,、東河戲,、四川胡琴、云南戲,、廣東粵劇,、廣西桂劇、南寧邕劇等,。
2,,以民間小曲發(fā)展而來的“二小”或“三小”戲的分布情況。
柳子類:有山東柳子、陜西迷胡,、河南曲子、江蘇柳琴等。
秧歌類:有河北秧歌、陜西秧歌、山西秧歌,、山東肘鼓子,、拉魂腔,、二夾弦、山西,、陜西、內(nèi)蒙古的二人臺,、浙江的篤戲。
落子類:有東北落子、唐山落子,、北京蹦蹦,、河北武安落子,、山西上黨落子。
花鼓類:有湖南花鼓,、湖北黃孝花鼓(楚�,。⑻煦婊ü�,、提琴戲,、梁山調(diào),、恩施燈戲、襄陽花鼓,、遠安花鼓,、江西采茶戲,、安徽皖南花鼓,、淮北花鼓、黃梅戲,、倒七戲,、泗州戲,、江蘇揚州戲,、江淮戲、廣西采調(diào),、四川花燈、云南花燈,。
灘黃類:有江蘇蘇灘、常錫文戲,、上海灘黃(滬�,。�,、浙江杭灘、金華灘黃,、湖州灘黃(湖�,。幉S,。
解放前后,,據(jù)統(tǒng)計,全國約有三四百種地方戲曲分布各地,。這是一支龐大的戲曲大軍,,這是一個以地方擁有實力,區(qū)別于任何戲劇文化的戲劇實體,一種特殊的文化現(xiàn)象,。各族人民之間的地域差別,,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化,這種差別與不同,,既有互相滲透與融會的一面,,又有各自獨立與相互拒斥的一面。因此,,誰興誰衰很難預測,,只有競爭是不可避免的。
三,、從未來前景考慮:關(guān)注地域文化和域外文化的融入和輸出,,對于思索戲曲未來,認識“揚棄舊質(zhì),,發(fā)現(xiàn)新質(zhì)”都具有特別重要的現(xiàn)實意義,。
中國戲曲做為中國文化的重要部份,更多地體現(xiàn)了民族和地域的特點,,藝術(shù)中的地域性特色,,已經(jīng)受到廣泛重視。但來自域外其它國家的文化藝術(shù),,更有深入認識的必要,。因為域外文化的影響,正從另一側(cè)面不間斷地剌激,、改變著我國文化的現(xiàn)狀,。故而,研究這種融入和輸出的不可逆性,,對于拓展視野開創(chuàng)未來,,更顯迫切。
(一)解放后戲改工作的成就和失誤,。
1951年5月5日,,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(fā)出《關(guān)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,具體闡釋了戲曲改革工作的內(nèi)容和政策,。這一空前的轟轟烈烈的戲改運動,,把自為的戲曲納入了人為的軌道,從此開創(chuàng)了中國戲曲的新天地,、新紀元,。
戲改工作的最大成就,是規(guī)范了戲曲的自為狀態(tài),。劇種根據(jù)劇目,、聲腔及從業(yè)人員的情況,,定了名定了制,定了從業(yè)人員的在冊身份,。劇團確立了歸屬,,成了國家建制的一部份。全國共有三百多個劇種,,從此,,在政府統(tǒng)一管理下,有條不紊地進行登記,、清理,、改建等等工作。這場群眾性的革新運動,,使全國很多劇種恢復了青春,,許多民間文藝得到記錄、整理,、加工和流傳,。中國戲曲遺產(chǎn)極為豐富,批判地繼承任務繁重,,對于麻醉,、毒害人民的封建性糟粕必須剔除,保存其民主性精華,,在新的基礎(chǔ)上,加以改造,、發(fā)展,。戲改之后,劇團工作欣欣向榮,,藝人受到尊敬,,演出活動也十分活躍,戲曲藝術(shù)在人為的光環(huán)照耀下,,確也向前闊步,,走出了新的步伐。
十七年的戲改成就,,創(chuàng)作了一大批為人注目的好戲,,如《祥林嫂》、《星星之火》,、《節(jié)振國》,、《血淚仇》、《紅燈記》,、《沙家浜》,、《智取威虎山》,、《紅色的種子》、《羅漢錢》,、《雞毛飛上天》,、《李二嫂改嫁》、《朝陽溝》,、《滿意不滿意》,、《奪印》、《三滴血》,、《姊妹易嫁》,、《女駙馬》、《團圓之后》,、《春草闖堂》,、《拉郎配》、《天仙配》,、《十五貫》等等,。
然而演員的技藝,在改制之后,,并無多大建樹,。“唱”沒有超過前人,,“做”也表現(xiàn)平平,,更不用說那些演員的絕活。雖然也有冒尖人物,,但多數(shù)是舊社會培養(yǎng)的人才,,不能算是改制后的成就。中國觀眾看戲,,一要滿意那個劇本的故事,,二要看演員表演的絕活,而后者尤其重要,。戲改之后,,重視編創(chuàng)的教育作用,特別是重視劇本的政治傾向,,而輕視演員的一技之長,,或者是忽略對演員在這方面的培養(yǎng),總之身懷絕技的人材,,漸趨稀少,。俗說“不看戲?qū)?此嚒�,,沒了這方面的表演,,戲曲好像少了一條腿,,那干巴巴的故事,只看一遍就夠了,。為什么,?這得從兩方面找原因。一是演員隊伍的訓練偏重演劇本中的人物,,而不注重用什么“手段”去演,。自引進斯坦尼的表演理論后,演員的自我修養(yǎng)在提高,,老藝人的那一套,,反而被人認做是不科學的方法,后來干脆不屑一顧,。另方面我們的評價標準在變,,評一出戲、評演員的表演,,都以劇本為中心,,很少考察觀眾是喜歡劇本,還是喜歡演員用獨特的技藝去演那個劇本中的故事,。甚至不尊重老藝人的創(chuàng)造,,認為老藝人掌握的那點絕活,和編創(chuàng)的新戲掛不上鉤,,用不上,,就算用了,也格格不入,。
戲改前后,,一批批文化人充實到劇團里來。他們帶來了新的理念,。從當時的戲改要求看,基本方向是正確的,。但從戲曲的發(fā)展規(guī)律看,,他們又很少考慮戲曲應該怎么建構(gòu)。他們只認為,,戲要有鮮明的主題,,立意要好,要注重文采,,提高戲的品位,。這個想法本不錯,問題是戲曲原本的藝術(shù)方法,,不能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,,而不予尊重,。什么是戲曲的藝術(shù)方法呢?其實說白了,,就是“不能搞得那么實”,。寫實方法不是不能用,而是不能排斥“虛實相生”的美學原則,,一切都變得鐵板一塊了,,那還有什么回旋余地呢?新戲再好,,也要留有空間,,否則只能是扼殺演員的靈性,去遷就寫實的劇本,。戲曲觀眾看戲,,要求表演劇本的同時,還要有機融入演員的技藝,,增強戲劇的可看性,。這個可看的要求,包括演員唱,、做,、念、打的技巧,,甚至是與劇本無關(guān)的個人絕活,。它域文化的融入,特別是域外文化的融入,,過去是由戲曲自身進行鑒別和選擇,,戲改之后是由一些不太懂戲曲規(guī)律的文化人代勞,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,,好心沒能成好事,。
(二)外國人眼里的中國戲曲。
中國戲曲走出國門一事,解放前就有。梅蘭芳訪問西歐載譽歸來,,成為當時中國戲曲界的杰出代表。他的大獲成功,,皆源于他個人的才藝:“唱”、“做”和“舞”,。一個男子漢表演一個絕色美女,,這本身就是個不可思議的絕活,更不用說,,他是用維肖的唱腔和柔軟的肢體去表演人物,。斯坦尼看后用贊賞的口吻,,描述他對東方戲劇藝術(shù)的崇敬;布萊希特則說,,他從梅氏的表演中,,找到間離理論的源頭。還有之前之后,,日本朝野上下三次邀請梅氏訪日,。
解放后,走出國門的事,,幾成常態(tài),。但最受外國人歡迎的戲,大多是武功技藝特別出眾的戲,,如《孫悟空大鬧天宮》,、《虹橋贈珠》、《三岔口》等等,。原因很簡單,,好看、驚險,、剌激,。他們坦言說:這是一種終身難忘的從未有過的藝術(shù)體驗。
出國本是換個環(huán)境演出,,但這是我國地域藝術(shù)一次次實實在在地輸出,。融入是我們選擇人家,輸出是人家選擇我們,。為什么我們選擇人家的是不對口的藝術(shù)方法,,而人家選擇我們,卻是自家不予重視的絕活,。
(三)文革十年的無為,。
文革十年所有劇目被當做文藝黑線的產(chǎn)物,一棍子打死,。八個樣板戲,,特別在劇本上做足文章,強調(diào)“主題先行,、三突出”,還在“文學性”,、“戲劇性”,、“音樂性”上,拔高身價,,戲曲再次被人為地擺布著,。引入交響樂伴奏,,還搞了鋼琴伴唱,看起來新鮮,,實則及表不及里,,未能從戲曲內(nèi)在要求和觀眾接受層面,這兩個方面深入下去,。因此,,浮光掠影,不可能做大范圍的融入性嘗試,。
(四)文革后,,戲曲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,加快了融入和輸出的節(jié)奏,。
新時期域外文化的涌入,,來勢洶洶。這不是融化吸收,,而是某種程度上的強行取代,。戲曲的競爭能力,在猝不及防的情勢下,,遇到了空前的挑戰(zhàn),。這次是戲曲本身的先天不足,在文藝思潮大涌動,,在現(xiàn)代傳媒興起和滲入當代生活的環(huán)境下,,一步步敗下陣來,幾至沒法應對面前的現(xiàn)實,。西方現(xiàn)代派文藝思潮的沖擊,,使戲曲界十分茫然。是接受還是慢慢融會,,是反對還是堅持固守,,一時間居然也引起了方向性的混亂。
新編川劇《潘金蓮》的出現(xiàn),,率先以接納這種影響的態(tài)度,,從形式上開刀,搞了表率式的獻演,。這在當時確實是很轟動的一件事,,行內(nèi)議論紛紛,大多數(shù)取支持肯定的態(tài)度,。但沒想到拿到市場上去檢驗,,卻反響冷淡。一方面是先知者要顯示自已的先覺,另一面是基本群眾抓耳撓腮沒法理解,,如強行融入,,必然適得其反,最后只好緩行,。
過了幾年,,戲曲家族平心靜氣回過頭來想想這事時,又出現(xiàn)了都市新淮劇《金龍與蜉蝣》,。這次盡管融合的還是域外的結(jié)構(gòu)和形式,,但它十分重視淮劇的唱,淮劇大段的堆字垛板,,是老演員的絕活,,劇中多處給了演員表演技藝的空間,因而它的演出基本上獲得了成功,。
這兩個例子,,都是有全國影響的大事。但這是有條件的,,一般的劇團是沒法應承這種融入性的嘗試,。因為戲曲不景氣的時日,已拖得太久,,政府又有甩包袱的安排,,人心浮動,實難有什么作為,。怎么會走到這一步呢,?主要是大環(huán)境下的文藝競爭,以及戲曲本身的先天不足所造成,。
什么是戲曲的先天不足,?指的就是戲曲自身的競爭能力。戲曲由國家統(tǒng)一定制以后,,看起來是好事,,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問題。包下來了,,可推不出去了,。就是說,在它從“自為”狀態(tài),,向“它為”狀態(tài)轉(zhuǎn)變時,,就注定了其后來不具備“經(jīng)風雨,見世面”的競爭能力,。自為狀態(tài)時,,戲曲必須保持一技之長,時刻不忘競爭,否則就會影響自身安危,。比如,乾隆時的六大班敗于魏長生,,十年后魏長生又敗給了四大徽班進京,。四大徽班為了使自己長久立于不敗之地,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對策,,不間斷地博采眾長,,后經(jīng)幾代人的努力,才形成聲腔技藝十分完備的大劇種:京劇,。而定制以后的狀況,,特別是眼下抱在懷里的新一代,只知埋頭唱戲,,而不懂競爭,,更不知何為風險和落寞。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個內(nèi)在的缺陷,,而不能事過境遷不敢正視,。
由于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,戲曲輸出的機會增多,。很多人見識廣了,,知道自已家里的家底,在外國人眼里有多重的的份量,。因此開始重新審視戲曲的價值,,人們不知不覺,也不知是為什么,,就這樣找回了自信,。加上外國洋學生專門來學的人,逐年有增無減,,戲曲藝術(shù)從另一個方面看到自已的希望,。于是融入和輸出的相互作用,使古老的戲曲正經(jīng)歷著空前的震蕩和選擇,。也許將有一批有志于變革的后行者,,以開拓前行的足跡,去創(chuàng)造新的未來,。
(五)揚棄舊質(zhì),,發(fā)現(xiàn)新質(zhì)。
戲曲“合歌舞演故事”的藝術(shù)形態(tài),,究竟還能延續(xù)多久,,誰也無法說清。戲曲理論的條條框框能否松動,也無人表態(tài),。但是戲曲演員唱,、做、念,、打的基本功夫,,只能加強不能削弱。特別是形成個人風格流派的絕活,,和那些蓋世的武功,,都是戲曲特有的具有非凡魅力的技藝,沒有它的存在,,那就是戲不象戲,,技不象技的另種藝術(shù)了。說它是“話劇加唱”,、“中式歌劇”,、“現(xiàn)代戲曲”、“戲曲現(xiàn)代戲”都可以,,也許這也是一條路子,,但它已是戲曲的變種,沒有揚棄的實際意義,。而戲曲最具魅力之處,,是從技藝去結(jié)構(gòu)故事。例如:為了表現(xiàn)兩個人在黑暗中的搏擊,,傳統(tǒng)劇目中就有《十字坡》,、《三岔口》等,而能演《十字坡》,、《三岔口》的,,必定是有武功底子的。這就是戲曲穩(wěn)定的舊質(zhì),。揚棄不是否定,,揚棄也不是一成不變,揚棄是在舊質(zhì)基礎(chǔ)上的一種創(chuàng)新,。
發(fā)現(xiàn)新質(zhì),,那是指過去所沒有的東西,按戲曲的規(guī)律予以考慮或接納的新玩意兒,。黃梅戲的唱,,與徽調(diào)同源,分道揚鞭之后,,徽調(diào)固化成嚴格的板腔體,,而黃梅始終在民間傳唱,,沒有固定的格式。自由優(yōu)美的旋律,,口語化的唱詞,,與通俗音樂的唱法十分相近,這就是人們發(fā)現(xiàn)的新質(zhì),。于是黃梅頻頻出現(xiàn)在通俗音樂會上,,就是合乎情理的事了。反過來黃梅引進通俗音樂,,也自然是可行的利用了。唱是一種技藝,,唱得好,,唱得絕,也會使人傾倒,,也會使人流連忘返,。根據(jù)唱,發(fā)揮唱的藝術(shù)魅力而結(jié)構(gòu)的劇本,,也是為體現(xiàn)技藝為目的的,。
因此,是不是可以下個斷定:“技藝才是藝,,無藝難成戲,,戲里有絕活,是技又是戲,�,!边@是京劇老藝人的經(jīng)驗之談,他們說:“本子再好,,也要看演的功夫,,舊社會就是靠功夫,走南闖北�,,F(xiàn)在好了,,吃現(xiàn)成的,編個劇本就齊了,,跟著演吧,,要功夫干什么?”
話不說不明,。說到底,,沒有什么現(xiàn)成的良藥,可以包治三百多個劇種的“百病”,。劇場方式的蛻化,,不等于沒法當眾表演,,電視方式的影象,也只能是影象而已,。路怎么走,,自已選擇。更況地域新文化不斷興起,,不斷更替,,不斷延續(xù)的事實告訴我們,當前戲曲面臨的是一種世界范圍的汰洗,,優(yōu)勝劣汰的自然規(guī)律,,也適用于觀察戲曲的生態(tài)和現(xiàn)狀。那種依賴政府維持下去的想法,,現(xiàn)在看來也只能是救急,,而不能救本了。競爭是殘酷的,,肯定有一部份劇種,,在競爭中淘汰出局,而另外生存下來的,,必定是競爭能力,、競爭條件、競爭資本都有充分準備的一小部份,。它們肯定有它們存活下來的道理,,它們肯定有它們自已的絕招。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(zhuǎn)移的客觀事實,,讓我們拭目以待,。
(全文發(fā)表在《劇論》1998年1期17—24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