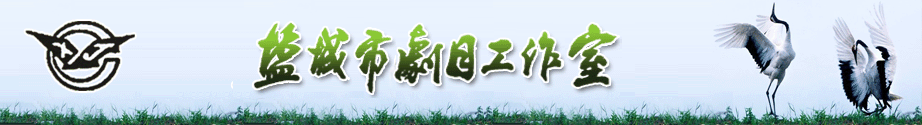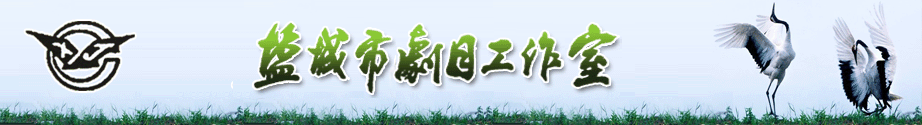�� ��
Ҫ�о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x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IJ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IJ�ͬ,�����F�ڑ��L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ʹ,���Y�֚��ᱯ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o�^��,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mȻҲ�ڄ�����Ⱦ���˹����ĵđn���cʹ��,���I����еı����Շ�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�һ���F�A�ĽY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β�͡��@һ��Q��żȻ,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IJ���P(li��n)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ġ�
�ڹŴ�,���Ї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δ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c���y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D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Ó���y�ĵ�·��Ȼ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IJ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·��Ȼ��ͬ��
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wϵ,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ϵ۵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ؚw�ϵ۵đѱ����屾�A�J����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Ǜ]�е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֮�f�����ڬ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y�Ԍ��F,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u)��Լ��?chu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ϣ�D�˺�����ǰ�Ͱ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ȱ����Ԓ�еı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ӡ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υ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D�˵ij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˼�Є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Ĉ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H�ǿ϶�����rֵ��Ҳ�ǹ�ϣ�D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ķ�ӳ,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ڹ�ϣ�D���_�R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ʥ��,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հ����,���@Ҳ�����Ӱ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Ȼ��,�����c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֮�g��ì���ǟo���{�͵�,���@һì�ܾ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ܡ��ڳ�M�n���Ĭ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ӵĞ��y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ü����Եľ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Ͳ��ҕr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һ�N�o���{�S���ѵĿ�ã�к�ʧ���,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R�r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Ď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e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ı�Ȼ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ǰ,�������֟o�εذ����g�ı����w�Y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�⡣���F�ڑ��Єt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¼��˴��g���б�Ȼ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,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ɟo���[Ó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ˣ���ϣ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\�Ķ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Į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ݺ��^ʧ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؞��ʼ�K�����\ע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Բ��ݻرܵķ�ʽ�ѿ��y�����ڒ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γɟo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Y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ğo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Ē�Ó�c���\���y�Գ�Խ��ɹ�ϣ�D�����Ě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֪�o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مs���x�o��Ŀ����гɾ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ʹ��a�����ˡ��z���c�֑֡��ĝ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γ��˴�ʹ��ˇ�g�L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˹�ڃ��r��ᔴ��p�_���ڻ�Ұ,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h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l(xi��ng)��K߀���y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ע���ďs��Ȣĸ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ڄ���,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˹��һ�В�Ó���\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һ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Kֻ�ßo�ε�ŪϹ���ѵ��p�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o���[Ó�����`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K���o���[Ó�Ԛ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\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߯�ݳ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ć����C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鲨������˹�İ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ʹ���`�õ���Ϣ,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Ȟ鳼���֞���õ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ă��y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o�ζ����B���Ŀ���,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ء��ж���˹����鰢٤�T�r֮�ӣ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ȥ�ĸ��H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Լ���ĸ�H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ض��qԥ�r,���K���ٶȰ��Լ����О�ϵ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,���Ŵ̳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˱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x��һ�����˺�,������Ȼ�ڃɷN����rֵ�ĊA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ĥ,�����،����Ó��ͬ��,�����Wِ�_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ķ�R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ҁ����ȟoһ����,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ͬ����,���Ŵ��Ї���Ҳ���Լ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粻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ڬ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硱,���Ї��˚v�������ӌӵ��ڷ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ڷ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,���vʷ�ϟo���ε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Pϵ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ڷ��Pϵ�����ɵľW�j֮�С��@���ڷ��Pϵ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˵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,����ҌW�f�ɹ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硱,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Ҫ�_����Ŀ�ˁ��_�����˵��˸�ɾ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ҵČW�f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w�c���w����ͨ�ĵ�·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˼�S��ʽ�Լ�ˇ�g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Ժ�ǧ�ٴ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ҌW�f��ijЩ����,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ͬ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硱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܌W�wϵ,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粻ͬ���Ї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`���ԡ��ľ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ărֵ�͌��F��;��,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Ї��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һ�N��ʡ���ǻ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Ԭ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c,���錍�F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Ŭ������Ҋ,���Ї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w,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Ȼ�l�����挦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t�����턓(chu��ng)��̫ƽʢ��,����һ���棬�ֿ��Ǐ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·,�������t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w�F�����ărֵ,����ӳ�ڑ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ڛ_ͻ���@�N�_ͻ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О�ʄt�c�F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x�ڂ��w�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Ă��˹����đn���cʹ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ϳʬ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,����ˣ��Ї����б��F�IJ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ܵĽ�¶�͑K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dzɾ͂����˸���D�y�c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ࡢʹ�����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o�V�ēP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ԩѩ�u,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ڈF�A�_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Ķ��w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N�ͳ�M�����c�ԏ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͵đ��١��]��ԩ��,�����и]��ԩ��ε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c�R��ǰ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Ը----Ѫ�R�Ҿ������½�ѩ,�����ݴ�����һһ�`�,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ӵصı���o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֮��I,����ԓ���ĽY�օs���丸�]���±����참,������ƽԩ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OӋ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ĽY�����nj��]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x�CȻ�����`�c�О�Ŀ϶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Ƶİ����c���P��ͬ��,�����wؑŮ���в̲��ؓ�wؑŮ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ؓ븹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ؓ�鱳�x�ߵ��{��͑��,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µ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w�Ϲ����г��e�˶�ʮ�����ԩ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,���mȻ�x���_����һ���t��,��Ҳ�ǿ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ēQȡ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ڄ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ărֵ,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еġ�ꎸ�Ӎ�顱һ�ۣ����Ɛ��Ј�����g�ڼ����쵽�����ꎲܵظ�,�����w�õ����조��ּ���ͻʵ��t�����p��ƽ��,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˼����f�o���^��,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`�Ď�����ͬ,���Ї��˿��ǏĂ��w�О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·,���Ї��˺����Џصı��^���x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Ø��^��չ��δ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R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͈Զ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ٱ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չ�F�˵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Ȼ�Ü��ͬ�r,���ְ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ĈF�A�Y�֣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̵Ę��^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w�F����ij�Խ�����`�Ľ��,����ˣ��Ї��]�Џصı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T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غͱ����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һ����F�A�ĽY��,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β�ͣ��o����ϣ��,��ʾ���Թ���,���w�F�e�O���ϵ��M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Ї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ˏ�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T��Ĺŵ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ڬ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^��и��Ŭ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еõ����F�Ϳ϶�,�,���ĵ��ͤ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Ԃ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c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ȥ,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ܑ{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ϲ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F���Đ����ڬF���К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đn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F�A,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擴�Đ����ܵ�ĥ�y,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ʿ��Т�ĸ���ӵ�,���Kʹĸ�H�@�ý��,��λ���ɰࣻ���ɼtӛ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꼃�p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K�õ��۵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^���õ�һ������ο��ĈA�M�Y��,��
��ʮһ���o�Ľ��죬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l(f��)չ,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Ó���ڷ��Pϵ���_�W,��Ҳ�P���˹��˽��I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硱,�����ǣ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C�M��,�����H�o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߀�،�Ӱ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֮��,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Ļ�,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҂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,����F�A�Y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嘷�^���x����;���Խ�ڑ��еı��F,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ڑ��еķ�ӳ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ԓȥԑ�y��,������ԓȥ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,��